“北京大学佛学研究系列讲座”第30讲之“佛学院体制的百年历程”,于2022年5月13日晚7时至9时30分线上举行。主讲人汲喆教授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赖岳山教授全程担任讲座主持人,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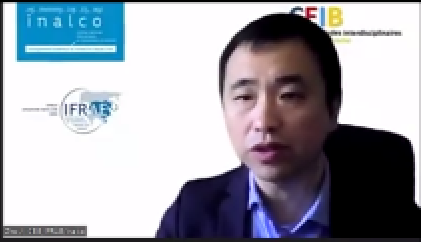
讲座开始前,中心主任王颂教授简要介绍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与本讲座的关联。接着,他重点介绍了汲喆教授的研究及其所在机构的情况。
汲喆教授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任教。该学院始创于1669年,是欧洲上最大的语言与文明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教授100多种语言,其中文教育开始于1840年,目前是全欧洲唯一在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中均设置中国佛教课程的大学。汲喆教授在多方支持下,于2016年组建了“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Bouddhisme, CEIB,并任中心首任主任。CEIB是法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学术性的佛教研究中心。该中心由法国在相关领域最负盛名的三家学术机构共同创办、合作管理,它们分别是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又译法兰西学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
汲喆教授及其所在机构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将通过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共同推进“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研究。
(一)讲座的旨趣、基本假设与历史情境
汲喆教授勾勒了20世纪中国“佛学院体制”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其中的支配性力量,进而指出“佛学院体制”因现代性的介入而带来的“学-修”矛盾。其研究旨趣在于从社会学层面来探讨近现代汉传佛教中“知识-权力-资本”的分配和流动,其研究的本质仍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历史学,但这种社会学是以恰当梳理历史事件为前提的。
整个讲座,通过梳理以下六类事件而展开:1、传统(汉至清末)宗教与教育的关系;2、佛学院在佛教教育现代化中的地位;3、武昌佛学院的示范作用;4、1953-1966年间“中国佛学院”的角色;5、1980年之后佛学院体制的演化;6,“学-修”矛盾的制度根源。
汲喆教授首先指出,传统中国教育和宗教两个领域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处于未分化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建立在传统宗教的废墟之上的。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连同此前“癸卯学制”的颁行常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教育正式确立的标志。而这一学制的改革,不仅引入了新的管理体制、教育方法和学习内容,进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中文化资本的价值标准和积累方式,同时也打破了儒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政治和教育三位一体的格局,直接导致了制度儒家的解体。另一方面,自1898年开始推动、而后在民国初期声势渐大的“庙产兴学”(或称“毁庙办学”)运动,则令佛、道教以及民间地方信仰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场强行征收寺院动产及不动产收益用于兴办新式学堂的政治-社会运动,配合反对“迷信”的话语,使大量宗教资本转移到了政治权力和那些对传统宗教抱有敌意的地方精英手中,不仅破坏了杂糅大小传统、混融各种仪式和观念的中国民间宗教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在实质上否定了这种宗教存在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庙产兴学”运动甚至意味着“中国宗教”在民间社会自成一体的传统体系的终结。
但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教育与宗教既有分离与对峙,也有交错与整合。知识/权力分配制度的转变,特别是有关传承理念、教—学实践和师徒关系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宗教之社会形态的转变。而现代教育的建立恰恰能为这种转变提供新的资源与动力。在现代教育中,合理化的学校体系是教—学实践的基本组织方式。这种方式一旦为宗教人士所吸纳,难免要在“何为传承的正确内容”、“何为传承的恰当方式”以及“谁为传承的合法主体”这三个问题上引发争议,甚至由此更动神圣、知识与权力这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改变宗教场域的秩序。佛学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二)“佛学院体制”:类型及各时期的政策支持
汲喆教授区分了“佛学院体制”的类型。他认为,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三种运动最引人注目。首先,庙产兴学运动迫使僧团团结起来保护寺产,并主动将现代学校的教育形式引入寺院,甚至开始投资世俗教育。这不仅促使僧团首次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利益团体形成了跨寺院的联合,也更新了寺院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其次,以杨文会、欧阳渐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借助以现代理性主义的文献学为基本内容的佛学,不仅为受到太平天国运动严重破坏的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而且以学术与出版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于僧伽佛教的自主性的现代居士佛教团体。第三,在僧团内部,以太虚为领袖的改革派僧人,则试图通过建立佛学院培训和动员青年一代僧侣,进而改变整个佛教的面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太虚的佛学院促成了佛教教育的范式转换,建构了“学僧”这一新的身份,同时也更新了佛教共同体与处在变革中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
进一步,汲喆教授还分析了佛学院的办学许可。他发现,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再到1949年之后(此一时期分为两个办学阶段,下详),不同时期的政策对佛教办学有不同的认知和规定。北洋时期不加干涉,较为自由。南京国民政府则着力于重新规划全国性的现代教育体系,不太支持缺乏同等水平的僧教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则由中央政府支持,创办了“中国佛学院”,该学院从1953到1966年间培养了一批僧人;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赵朴初的筹划下,从全国性的、唯一的“中国佛学院”拓展出两家分院,同时,地方性的佛学院也逐渐兴起。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中国佛教协会原本期待实践一种“中央计划体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一体制从未建成,在一定程度上,佛教僧团的教育再度市场化了。
(三)修道与求知、传统与现代
据上历史分析,汲喆教授指出,“佛学院体制”所实现的“科层化”,实际上是现代性或理性化的结果,它直接冲击了传统佛教社团的运作机制。传统佛教社团,以“得道”“成圣”为主要目的、从“师徒印证”中获得“象征资本”以实现代际传递。其结果,汲喆教授总结为三种根本性的变革:改变了师生关系和学生的流动秩序;打破了以寺院、法脉、同乡等为纽带的团体构成方式;出现了以“文凭”为“象征资本”的评价体系,但僧人的知识却不容易企及现代教育体制所培养的人才,相应地,僧界亦对现代佛学院的培养方式持有疑虑。一言以蔽之,这些变革和冲突被归结为“‘学-修’矛盾”,它简要地表现为“固化-流动”、“传统-现代”、“总体的道-有限之知”之间的冲突。
汲喆教授认为,佛教界内部对佛学院体制的批评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指出的问题——例如教学设计混乱、教师受教育程度底、能力不足等等——也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和表面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僧人对于佛学院的制度本身有一种根本的不信任,认为这种制度很难达到僧教育的真正目标,即培养信仰坚定、情操高尚的宗教导师。这种不信任产生了一种将“学”与“修”以及“学院”与“丛林”对立起来的话语,即认为佛学院的失败在于强调知识“学习”而忽视了宗教“修行”,在于学院没有依据丛林的传统加以组织与管理。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的汉传佛教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生生活丛林化”的要求。如今这已成为几乎所有佛学院的口号。但是,这些设想与改革并无法真正解决学与修的矛盾。汲喆教授指出,学与修的矛盾反映的其实是学校与寺院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寺院是“道场”,既要组织日常仪式,也要处理常规性的行政事务,并为在家佛教徒提供宗教服务。这些显然都不是旨在为青年僧人提供知识与文凭学院的目标。
不仅在分工、义务与权利上缺乏共识,佛学院和寺院各自的内部组织以及它们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也很不相同。寺院的住持与常住僧之间多有传统的师徒关系。由于这种无限期的委身和稳定性,常住僧组成了一种信念团体,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寺院本身。相反,佛学院则借鉴了世俗学校的科层制。私人关系并不是学僧入院学习的先决条件,学僧对寺院也没有保持长期联系的契约。寺院与佛学院这两种佛教再生产制度的差异与矛盾,经过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提纯,就被转译成两种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即学与修的矛盾。这种话语隐含地否定了“学”的宗教价值,包含着对学僧的宗教品格的成见。但事实上,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认定佛学院的学僧在遵守宗教规矩方面比一般僧人更差。
赖岳山教授全程担任讲座主持人,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点评。

讲座结束后,听众踊跃参与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新加坡佛学院纪赟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融道教授、东南大学张佳教授等学者发表了见解,一些听众也在发言栏提出各种问题,与汲喆教授共同探讨“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理论、制度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