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商業、宗教:佛教與全球化的歷史與展望
帝國、商業與宗教,看似毫不相關的三者,如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以此三者為主題,近期舉辦了“帝國、商業與宗教:佛教與全球化的歷史與展望”工作坊,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參與了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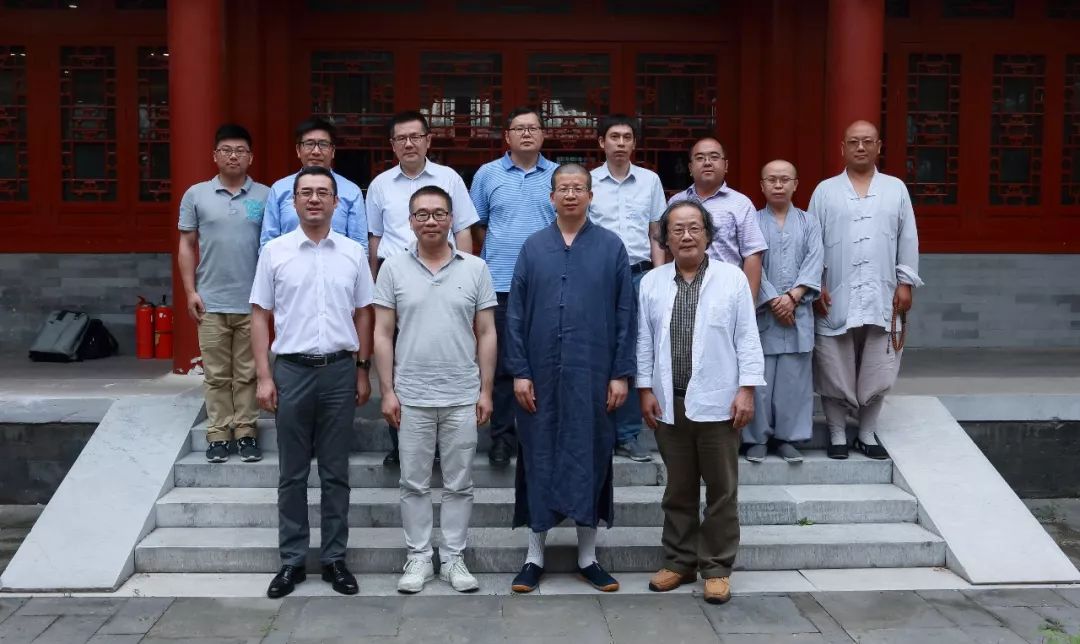
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王頌教授首先介紹了工作坊的主旨。他指出:帝國研究方興未艾,重新成為輿論和學術焦點,其直接原因是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波折,一些原本積極推動全球化的國家自認為成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那些受益國家,在內外洶洶面前也顯得躑躅不前,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一部分人重彈歐洲近代民族主義的老調,鼓吹民族利益和本土文化;另一部分人則對啟蒙運動以來成為主流價值觀的民主、自由、理性予以否定。這些都導致了對長期主導人類歷史命運的帝國的回憶和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帝國形態的憧憬。
在技術剝奪思想、力量代替審美的今天,帝國話題的崛起,或許可能成為越來越被邊緣化的人文科學的歷史發展機遇。因此,學者們希望不要將此話題限定於政治學領域,在大歷史、全球史的視域下,從更多維度來拓展思考的廣度和深度。帝國、宗教與商業,或許就是一個新的思考維度。自古以來,帝國作為一種無遠弗屆的大一統體制,必然匹配一種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識形態,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國有擴張期的衝動,對暴力與征服的崇拜;有收縮期的恐懼,對和平與維繫穩定的渴望,這些都將動員與耗費大量資源。在所有這些過程中,宗教武裝其頭腦,商業新鮮其血液。三者密不可分。工作坊基於以上問題意識,彙集不同學術背景的學人,以期多角度、全方位地發掘相應歷史資源,深化對此問題的理解。

陳金華教授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陳金華教授作為引言人發表了主題演講,他認為:任何世界性帝國的興起與擴張,無不依賴于龐大的環球商業網絡及提供普世價值的世界性宗教;二者可說是帝國騰飛的翅膀。帝國一方面需要商業的支撐,另一方面需要引領時代的普世價值體系;帝國的權力又與後二者形成一個相互關聯且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
帝國或多或少都表現出一種全球化的趨勢。這當中包括貨物的全球化、貨幣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但最重要的還是價值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企圖與帝國的擴張同步,其中也貫穿著多層次的矛盾與張力。其一,追求全人類福祉的普世價值與根植於集團利益的地域價值之間的矛盾,這是始終存在而難以避免的矛盾,在帝國過了上升期之後則更容易凸顯為主要矛盾。其二,主要依託於貨幣或者其他動產、旨在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的貿易文明,與主要依靠不動產的農耕、手工文明之間有一種難以協調的對抗。這兩對難以調和的大矛盾與大衝突最終導向農耕、手工文化對商業貿易文化的反噬,以及地域價值對普世價值的否定,進而帝國收縮,導致支撐帝國擴張的全球化崩解,這就解釋了帝國為什麼一定會有一個成住壞空的週期,為什麼最後都會走向解體,也向我們揭示了所謂的“帝國之癌”的來源。
佛教在歷史上曾經與數個大帝國發生過上述錯綜複雜的關係,特別體現在其為帝國全球化提供助力的方面。佛教之所以能發揮如此之功用,是因為其自身所具有的國際品格與商業精神。作為亞洲唯一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一開始就具有普世價值和世界主義情懷,所以雖然它起源于南亞卻不會拘泥于一時一地,不會止步于南亞或中亞地區,而是不斷向外擴張,最終橫跨整個亞洲。除了國際主義的品格,佛教還具有天然的商業精神。所謂“商業精神”,即謀劃財富累積、遵奉契約精神、拓展貿易空間、擴大商業規模的鍥而不捨的精神。佛教恢宏的傳播路線,差可比擬今日的“一帶一路”,自古以來就是“一帶一路”上商業活動的天然夥伴。佛教僧侶與商人的追求與使命固然不同,但商隊的駝鈴與僧人的錫杖卻常常交相鳴響在黃沙古道上。二者的聯合,有物質性的——如交通等技術手段,有精神性的——如商人尋求佛法的庇佑,多重原因,註定了佛教與國際貿易興衰一體的格局。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與佛教相伴的帝國擴張與全球化努力。從南亞次大陸的阿育王、迦膩色迦王,到中國的梁武帝、隋文帝,特別是武周帝國的則天武后,以及日本的聖武天皇、桓武天皇,佛教的海潮之音都回蕩在帝國的豪邁步伐中。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全球化所導致的發展瓶頸乃至兩難,以及舊的全球化領袖日漸走向保守與孤立,而新的全球化領袖尚未完全脫穎而出的窘境。由此,研究佛教與全球化關係的歷史,有助於探求漢傳佛教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源頭活水,有助於認識漢傳佛教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助力角色。

聖凱教授
清華大學哲學系聖凱教授發言的題目是:《佛教現代化與化現代——佛教與商業文明》。他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探討了佛教與商業的關係。所謂商業化問題,特指商業資本進入佛教道教領域,並借教斂財的現象。他指出:佛、道教的商業化問題目前成為政策和輿論關注的焦點,但在中國諸多宗教團體中,為什麼佛、道教的商業化問題最引人關注?他集中回顧了建國以來佛教團體的經濟發展情況,說明了商業化的背景。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後,寺院土地被沒收,原本擁有農禪並重傳統的佛教不得不開展一定的手工業、商業活動。改革開放以後,為了改善佛教界經濟收益異常窘迫的局面,中國佛教協會提出了自養事業的口號。各地寺院開始開辦素菜館、法物流通處,一些寺院還收起了門票。而如今,社會上確實出現了一些亂象,這實際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為了營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出現了寺院借貸、甚至承租等現象。行政部門的多頭管理,旅遊、文管、園林、宗教等九龍治水,也導致亂象難以根治。而由於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人們對佛道教又寄予了某種“代表傳統”的意象,這些都無形中放大了質疑的聲音。
商業化治理既是一種神聖的回歸,更需要一種教化的開展。戒律建構與詮釋了佛教的神聖性,成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為保證僧團和合、安樂、清淨的源泉,亦成為僧人的行為規範與僧團組織的運作制度。宗教團體本身要維護宗教的神聖性,依戒律進行治理;要與時俱進地發展,以國家法律法規為框架,規範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佛教界自身要認清寺院經濟的本質,通過修道和弘法,讓寺院經濟回歸“供養經濟”的來源;加強制度監督與審計,加強內部的集體決策與監督,讓寺院經濟不要成為“個人所有”,回歸“常住所有”。從大格局來說,商業時代是佛教從未遇見的根機,佛教界如果沒有提前反思與應對,就會真正被“商業化”,佛教必須有“化商業”的勇氣與智慧,這是兩千年農業時代佛教的結束,也是新時代佛教的開啟。其次,佛教界要對“新時代”有充分的認識,積極推進現代意義的佛教中國化——佛教現代與化現代。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對商業,提倡新的商業文明倫理。應當以制度為保障,回歸佛教的教化本位,就是要對這個社會潮流發出獅音,構建新的商業文明。
聖凱教授進一步指出,應該將佛教置於全球文明史的視野下予以考察,看看佛教與商業的關係到底如何。佛教是否具有天然的與商業結合的氣質,佛教思想中有無重商主義的因素;還是因為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受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而不得不與商業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劉屹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劉屹教授發表了《“末法時代”佛法與王法的關係——從靜琬題記說起》的報告。他以貞觀二年(628)靜琬石經山題記中一個缺字為線索,指出了一些記錄房山石經的傳世文獻,以及調查研究房山石經的佛教學者長期存在的誤解,即他們大都認為靜琬發起刻經運動的目的是為了防備未來再度發生的“法難”。細繹靜琬題記的原意,刊刻石經的目的,並不是為在下一次發生“法難”時如何保存佛教經本,而是為了在千載萬代之後,佛法在人間面臨徹底消亡命運之時,還能保證有佛教經本可以傳世。由此提出的問題是:世間王權對佛教的態度,究竟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佛教的歷史命運?按照佛教自身的邏輯而言,世俗王權或王法或支持、或破壞,都不能決定佛法的命運。但是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下,中國佛教有時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注意調整佛法與王法的關係。與靜琬大體同時的費長房,取用了與靜琬認知不同的“末法”何時開始的計算方法,從而避免了把隋代認作是“末法時代”,把隋文帝置於“末法時代惡王”的尷尬境地。

孫英剛教授
浙江大學歷史系孫英剛教授《布發掩泥的北齊皇帝——源自犍陀羅的燃燈佛授記在中土的政治宗教意涵》一文,強調歷史圖景不是單線的、單畫面的,從不同的視角,會看到歷史真相的不同層面。南北朝時期是佛教繁榮的時期,從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會帶來新的歷史資訊。除了跟轉輪王有關的“皇帝菩薩”、“菩薩天子”、“月光童子”等有關的一類理念外,北齊文宣帝高洋有一種特殊的操作——他把自己打扮成燃燈佛授記裡“布發掩泥”的修行菩薩儒童——也就是釋迦牟尼的前世。多種文獻記載,高洋視高僧法上為佛,自己布發於地,讓法上踐之。
早期漢文譯經從史源上來說具有高度權威性,漢文譯經對燃燈佛授記的描述符合犍陀羅的圖像細節。 燃燈佛授記這一理念,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在犍陀羅現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數量之多也令人驚訝,但是這一佛教藝術主題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見。儘管歷史上的釋迦牟尼沒有到過犍陀羅,但是他的前世被放在了犍陀羅,而且這個故事儘管是佛本生故事,但是卻被放在了佛傳故事的開端,成為佛教神聖歷史的起點。通過燃燈佛的授記,儒童正式獲得了未來成佛的神聖性和合法性,為之後歷經諸劫轉生為釋迦太子奠定理論基礎。佛教的偉大志業,也都是從燃燈佛授記說起。在事實上,通過燃燈佛授記,將佛教的開端重新定位在犍陀羅。燃燈佛授記和彌勒信仰關係密切。彌勒授記也是從燃燈佛授記接續的,過去已經成功的授記,為彌勒授記提供了歷史合法性。中國佛教將燃燈佛、釋迦牟尼、彌勒視為三世佛。以釋迦牟尼為中心,燃燈佛授記和彌勒授記構成了過去與未來的準確對應。已經成為“歷史事實”的燃燈佛授記,為彌勒信仰提供了堅實的邏輯基礎。
北齊以佛教立國,佛教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慧光——法上這一地論僧團在北朝末期佔據主流;同時來自犍陀羅地區的高僧那連提黎耶舍在文宣帝的政治宣傳中地位重要。東魏北齊時有關轉輪王的理念極為普及。燃燈佛授記的藝術主題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廣為流傳,比如在雲岡石窟,燃燈佛授記的題材就達 10多幅之多。雲岡18窟主尊很可能就是燃燈佛。 在布發掩泥的操作中,法上是燃燈佛的角色,那麼布發掩泥的高洋,就是自比在此世修行菩薩道的儒童。法上為高洋授菩薩戒以及授記,就轉變為佛為高洋授戒與授記。高洋自比修行菩薩道的儒童,就賦予了自己“菩薩”的身份——並且在遙遠的將來通過累世的修行,最終成佛。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土的轉輪王內涵,實質是踐行菩薩道的天子。不論是“皇帝菩薩”還是“菩薩天子”,都強調君主修行菩薩道的統治者的形象。這種意涵表述最為清楚的是武周時期新譯《寶雨經》。

余欣教授
復旦大學歷史系余欣教授報告的題目是:《建造樂土——吳越的佛國政治與商業社會》。他運用大量考古資料和域外文獻,考察了唐宋之際雄踞江南的吳越國憑藉佛國政治和商業網絡經略一方;作為意識形態和宗教實踐的佛教信仰如何在國家戰略、地域社會、利益集團、精英階層和普羅大眾之間達成合致關係,共同建造東南樂土。
余欣指出,吳越作為唐宋變革期的地方政權的雙重性格值得重視:一方面恪守保境安民,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的立場,確保經濟繁榮,社會安樂;另一方面具有世界主義情懷。在北方先後經歷唐武宗滅佛、周世宗毀佛的情境下,東南一隅的吳越以阿育王傳統的繼承者自居,尤其是吳越國王錢俶“頗尊天竺之教”,“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批釋氏之典”,在位三十年間,不遺餘力推崇佛教,意在營造佛法昌盛的佛國。錢俶“奉空王之大教,尊阿育之靈蹤”,追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藏舍利之故事,兩次各造八萬四千金銅、精鋼阿育王塔,並在塔身內庋藏《寶篋印經》,廣布四方,正是對佛教世界主義的承繼。考古實物不僅發現于東陽中興寺塔、黃岩靈石寺塔、金華萬佛塔、溫州白象塔、里安慧光塔、上海青龍鎮隆平寺塔等吳越故境的佛塔內,而且在吳越國周邊、中原地區、日本平安時代佛教遺跡中,亦有發現,並且在日本史籍中留下詳細記載,在民間則出現數百座模仿阿育王塔的墓碑,而在韓國則有仿自吳越刻經的高麗本《寶篋印經》,可見其流風所被,在東亞世界影響之巨。
佛國並非統治者單方面造就,區域性和國際性商業網絡的發展,世俗供養的發達與地域社會興起,也貢獻良多。余欣認為,吳越佛塔出土文物是巨大的寶藏,並通過黃岩靈石寺塔出土的乾德四年(966)舍利容器銘文、墨書,王延煦施入發願文木牌,開寶七年(974)顧承達造石塔記,甲戌歲(974)彩繪貼金千佛磚及背面台州城下香客金太施捨供養題記,東方提頭賴吒天王線刻銅鏡勾當僧歸進舍入供養題刻等新資料的細緻解讀,具體而微地揭示了官民僧俗、士農工商是如何上行下效、合意協力營造樂土的。

李雪濤教授
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濤教授《十九至二十世紀上半葉全球信仰與知識的流動》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帝國、商業與信仰和知識傳播的關係。他指出:十九世紀以來,技術進步使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不斷湧現,特別是商業和民用輪船的使用,鐵路的鋪設,以及電報、電話的發明,真正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十九世紀在成為技術與商業革命的世紀的同時,也是一個信仰全球化的世紀。歐洲基督宗教的神職人員認為,他們行使著“文明化”的使命,向世界各地傳教。此時的宗教是除科學以外的大規模傳播網路的偉大締造者。
從十九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真正成為了一個所謂的“互動空間”,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特哈默所指出的那樣:“所謂互動空間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續發生接觸的區域,在這裡,儘管矛盾和齟齬時有出現,但是各種混合形式的新架構和新格局也在不斷形成。”東方的信仰和知識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也不斷影響著西方世界:印度哲學家辨喜于1894年在美國創立了第一個吠檀多學會,他本人被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聘為教授,隨後訪問英國、瑞士、德國等。在他之後,“瑜伽”風行世界。太虛法師二十年底末的歐美之行,開啟了華人歐美弘揚佛教的先河。這些都屬於信仰和知識互動時代的一部分。
實際上,自啟蒙運動以來,歐洲學者開始使用現代性的概念和預設,從而導致了現代的知識和分類一直都是建立在所謂現代與傳統、外來與本土知識的對立上。通過對這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知識遷移的考察,我們需要一種超越知識本身的研究,去甄別不同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參與到知識的生產及傳播過程中的。知識遷移永遠不是靜態的發展,而是一個文化間的動態調試、碰撞、融合的過程。因此,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樣,知識並非真理的反應,權力關係才是知識建構的主軸。只有在一個全球互動和去歐洲中心主義的前提下,我們今天才可能採取更適當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建構知識流動和產生的模式。

王勇教授
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的報告內容是:《東亞視域中的聖德太子——新出資料的解讀》。王勇教授認為: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在漢化過程中,迅速傳播至漢字文化圈周邊國家,形成東亞區域特有的宗教體系,一方面中國古已有之的信仰被重新書寫,另一方面東亞跨國交流的形式發生嬗變。南北朝高僧慧思在《立誓願文》中發出了乘願再來的預言,此後在東亞語境中被依次解讀為托生東方、再誕日本,直至定格為轉世成聖德太子。這一宏大的東亞轉世傳說,又促進了人員往來與物資交流。舉例說,慧思曾在齊光寺造金字《法華經》秘藏石窟,等待彌勒下生時再現人世;聖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即肩負尋覓這部金字《法華經》的使命。雖然據信由遣隋使帶回的《細字法華經》至今仍被奉為日本國寶,據學者考定實乃揚州人李元惠抄寫的唐經,但這一信仰確實在日本掀起了“入唐求書熱”。八世紀中葉日本的佛經總數甚至超過《開元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佛經被大量傳抄,促進了寫經業的空前繁榮。與此同時,以聖德太子“三經義疏”為代表,日本人撰寫的章疏也開始回流中國。據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維摩詰經》跋文,該經系聖德太子手抄百濟高僧帶到日本的“震旦善本”,再由遣唐使帶至中國輾轉而成的再抄本。雖然有關這部經的細節還需進一步考證,但慧思轉世為聖德太子的信仰,促進了東亞書籍的傳播、抄寫、再造,這或許也可以稱為由宗教所促成的“古代東亞物聯網”。

王頌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王頌教授《大佛開眼——佛法東傳與帝國的複製和建構》,以日本奈良時代營造東大寺大佛的歷史為背景,分析了在日本試圖效仿盛唐建立中央集權制帝國的過程中,佛教所發揮的作用。他首先以豐富的史料,探討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究竟是誰主導了大佛的營建。通過對聖武天皇、光明皇后和自唐回國的留學僧玄昉等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說明了大佛營建絕不僅僅是一場規模浩大的宗教活動,而是一項具有強烈政治目標的國家事業。王頌教授進而以大佛營建過程中陸續登場的幾位著名歷史人物為線索,進一步分析了佛教在帝國構建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如孝謙天皇、吉備真備和藤原仲麻呂的政治鬥爭;行基如何從朝廷指責的蠱惑民眾的“小僧”轉變為負責營建大佛的大勸進,並進而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大僧正;而玄昉和道鏡又如何從炙手可熱的權僧淪落為權力鬥爭的失敗者等等。通過對這些錯綜複雜的史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行基和玄昉、道鏡的行跡在表面上大相徑庭,分別被歸屬於民間僧和宮廷僧兩大陣營,但他們實際上都是政治與宗教相結合的代表。一方面有聲望的僧人成為專制君主以及貴族的鷹犬和工具;另一方面,懷有野心的僧人又利用與君主和貴族的結盟來覬覦權力。僧人參政體現了僧侶集團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所擁有的強大影響力,同時也反映了君主集權制尚處於不成熟狀態,僧人不得不時時捲入新舊利益集團的政治鬥爭。
最後,王頌教授認為:日本儘管在奈良時代全面效仿唐朝,進行了諸多營建帝國的努力,但最終並未能獲得成功。按照帝國的標準定義,它應該是不同政治體之間的一種差序結構,而當時的日本尚不具有有效控制他國或對他國施加影響的實力。更為致命的是,君主專制在當時雖然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仍然不能保持政治權威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貴族威脅皇權、架空皇權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與日本尚不發達的生產力水準有關,但與日本統治者選擇佛教而非儒教作為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有很大關係。佛教雖然可以為君主統治打造神聖光環,為帝國征服提供普世主義理念,但它不能有效地提供維繫統治秩序的等級制度,不能形成類似于儒生群體的擁有高度政治自覺性和忠誠度的統治集團。因此,日本雖然引進了諸如律令制等多項中國制度,但卻缺乏貫徹、維持制度的思想自覺和利益驅動。
營造大佛,無非就是以唐帝國為理想為藍圖,所以唐帝國可以說是上至天皇下至黎民百姓全體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然而正如佛虛無縹緲只在人們心中一樣,繁榮昌盛的唐帝國在現實的日本也只是一個未能實現的夢想。日本的帝國模仿與構建實際上以失敗而告終。

攝影:倪天勇